
《短剧开始了》
5月12日傍晚,37岁的潘丽云拎着行李箱和孩子一起,刚从广州四海城的“遇见大侦探”主题展览回到江西九江。
她习惯这样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穿梭。这既是工作的一部分,也是一种体面的逃离。去年这个时候,她还在湖北、安徽、江西多地跑演出,两年演了400多场科学剧;现在,她的日程上多了“找场地”“谈营地”“送盒子”这些低密度、低利润、低风险的事情。
“市场变了,节奏也变了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,像一个掂量路况的老司机。
潘丽云,10年教培人。两次创业,三次转型。她三年赔光150万,又在两年内赚回500万。如今,她即将站在新的拐点上。
在当下这个频繁变化、不再许诺稳定的时代,“成功”变成了一种流动状态,而“活下去”成了最可靠的目标。潘丽云的五年创业路,是一场在不确定性中反复适应、反复变形的实验。风口褪去之后,她选择不逃、不赌、不等待,以一个创业者最朴素的姿态,继续站在台上。
01
2018年的冬天,潘丽云站在教育创业的浪潮之巅。那时她是一家国际儿童科学教育品牌的市场总监,负责在上海繁华商圈扩张STEAM教育校区。彼时全国各地的投资人正在涌入素质教育领域,尤其热衷“创客”“编程”“机器人”“STEAM”这些极具未来感的词汇。这一年,资本用139起融资,砸出了素质教育49.67亿元的火热景象。一切都像挂在风口上的彩带,迎风而动,似乎谁抓住了,就能飞起来。
她不止一次在会议室里听到“教育的下一个风口”,也不断收到来自家乡江西的邀约,“把一线资源带回来,改变二三线城市的孩子”。那种召唤像是一种双重诱惑:既是创业机会,也是身份上的补全。2019年初,她离开上海,回到南昌,投身STEAM教育创业。
南昌的第一家STEAM学习馆落在红谷滩核心商圈,沿用她在一线城市熟稔的打法:先建空间,打品牌,拉动课程营收;再用科学盒子和寒暑假营反哺流量。“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有了。”她后来回忆说,“我们是真的相信,这会成功。”
一个学期后,问题开始显现。
“STEAM在南昌,就是五个英语单词。”她说。这里的家长对机器人课程充满疑惑,对创客空间没概念,愿意付费的群体稀少。学习馆招不满人,只能转向学校做低价的社团课程和公益科普。一学期课程下来,每名学生收费一千元,扣掉材料与师资,几乎不剩利润。如果潘丽云有预知未来的能力,她就会知道,留给她和团队的试错时间,有且只有一年。当然,没人能预见未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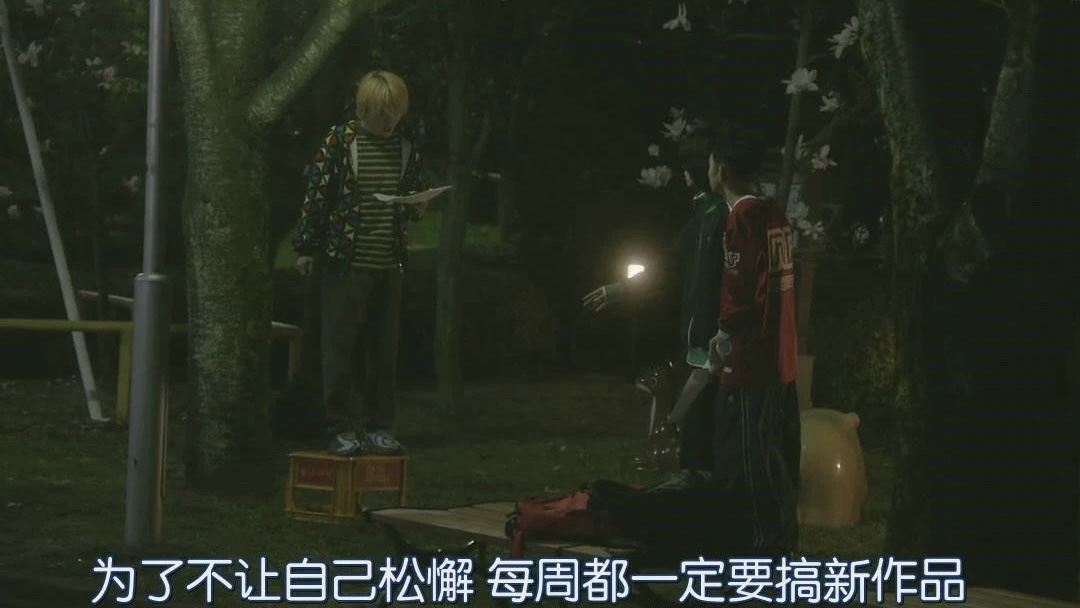
课程进校园了,却没有转化路径。公众号做起来了,却没能留存用户。他们仿佛搭好了一个演出舞台,却一直等不到观众。
2019年终盘点,团队账面亏损90万。团队中的大多数人还很乐观,觉得再坚持一学期就能“打开局面”。但她已经有些隐隐的不安。
社会学家乌尔里希·贝克曾创造出一个“风险社会”的概念:在“风险社会”中,结构性的不确定被包装为个体的“选择”,当“风险”变成常态,创业者们只得用冒险来对冲“没有选择”的命运,否则,他们将以“个体失败”的名义被叙述。潘丽云就身处这种荒谬的张力之中:政策让你回来,市场让你交学费,结构不保障你,社会却会说“你不行”。
当下的创业者,往往并非在寻找某种机会,而是在系统性的失序中试图构建一种合理的生活。潘丽云有些怀疑,“风口”是否真的存在。但她知道,风,是不为任何人停留的。而她,也正一步步走向那个无人可以预料的2020年春天。
02
2020年春天,教培行业一夜停摆。
春节刚过,疫情蔓延,学校停课,线下课程全面暂停。潘丽云原本打算在寒假期间冲一波营收,通过科学盒子和冬令营回血,却瞬间被拦腰斩断。
面对突如其来的停摆,她和团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盒子的研发上。两个新品盒子相继问世:一个是《病毒与呼吸系统》主题,另一个是《厨房里的科学》。后者受欢迎一些,探索十种厨房原材料,一套盒子可以玩七天,定价69元,下单的除了家长,还有学校、商超、银行。最终,这款盒子卖出300多套。在那个所有人都试图撑过去的时刻,这300多份微弱订单,仿佛是夜里稀薄的篝火。
疫情下,没人能真正重新布阵。她们靠着最低限度的人员配置、偶尔的线上合作维持运转,等着“春暖花开”。
结果等来的却是大水。2020年6、7月,南昌遭遇洪涝,STEAM学习中心被淹,墙面潮湿,器材发霉。她站在湿漉漉的教室里,看着教学板脱落、纸质材料起泡,心里几乎没有波澜。“当时已经被折腾得对‘意外’没感觉了。”她回忆。
2021年底,她关掉了STEAM学习中心,注销公众号和视频号。三年投入,亏掉150万。她回到九江,不再谈理想,也不再更新朋友圈的工作动态。她说,“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天。”

直到2022年3月18日,潘丽云在社交圈看到《卖了4套房,创业12年,如今负债1亿,无家可归》一文,作者是纽诺教育创始人王荣辉,她用“失败的Loser”“负债的骗子”自称,字里行间满是无法反驳的疼痛。一种难以言表的酸楚涌上心头,潘丽云转发分享了这篇文章,写道:“遗憾的同时,佩服这样坚守的人”。
那句“坚守”,她自己也反复咀嚼。她意识到:创业者不能总想着赢,更多时候是在与损耗博弈,能多熬一轮就是一场胜利。
她开始在九江到处走。八里湖畔、市博物馆、街角社区中心……像是在踩点,又像是在找寻方向感。九江,是她出生长大的城市,也是她始终回避的地方。
这座城有2200年历史,北枕长江,南望庐山,却是一个教育资源落差巨大的城市。在上海,一个孩子一周可以上四五节科学课;在九江,两节都难得,课程内容单一,实验材料稀缺。她的教师朋友私下说:“政策是有的,但现实是没戏。”
潘丽云还是要创业。这一次,不是寻找风口,而是寻找缝隙。她心里清楚,不能再做一遍STEAM学习馆的路子了。但还能做什么呢?她不清楚。她只知道:自己仍然想做内容,仍然想做教育,但一定要先活下来。
那时候,她还不知道,“教育”这个词,在她人生中即将换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式。
03
无论生活成了什么模样,总会被一丝灵光照亮。
有一次,潘丽云站在八里湖畔,看到市文化艺术中心外写着“唐宋名篇朗诵会”“红歌唱响九江城”的招贴时,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:如果把科学和戏剧结合,能不能创造一种全新的儿童教育体验?
这是她从上海的经验中生发出的灵感。在商超里表演科学秀、在学校里用戏剧做品牌推广,她早就熟悉这一套。但这次,她想倒过来做:以演出为目的,以教育为魂,面向家庭,制作儿童剧。
2022年6月,她找到新的合伙人莫莫,一位有戏剧背景的教育工作者。她们围绕九江地域特色打造原创剧目《昂戈鹿历险记》,串联起庐山、鄱阳湖等地理符号,用童话语调包裹自然知识。
她不惜花20万请专业话剧团撰写剧本、做表演训练。这是一次“跨界创业”的首笔学费。不问回报,只求站住脚。首轮演出走入社区和幼儿园,免费表演,积攒口碑。
之后,她开始将科学秀、物理秀与剧本融合,制作出《神奇物理秀》。2022年全年,这场演出只办了两场,常常因为“不可抗力”临时取消,收回的票款也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原路退还。
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23年春天。
疫情政策全面放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,文旅市场迎来井喷式复苏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成为新晋景点,淄博的烧烤让城市重新焕发流量魅力,贵州“村BA”点燃了乡村赛事的热情。整个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苏醒,走上街头、走进剧场、走向远方。
这股风也吹到了潘丽云这里。《神奇物理秀》爆了。她和团队马不停蹄地在江西、湖北、安徽巡演,仅此一个剧目一年演出超过400场。

门票分成、景区包场、演出费加分成——合作模式灵活多样。她最喜欢的是“包场”,虽然辛苦,一天演几场,但营收稳定、回款迅速。整场打包下来,单日演出费用能到2至3万元。
“从省会到地级市,再到县城,演出一站站下沉。”潘丽云记得,县城的孩子总是“哇”得最响,演出一结束就围上来追问:“那个瓶子怎么飞的?”“我能不能在家试试?”真正打动她的,不是营收数字,而是那份未被教科书熄灭的好奇心。
2023年全年,潘丽云团队实现营收500万元。她一度以为,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路。然而,她越来越不敢相信“正确”这个词。团队一直控制在10人以内,每人身兼数职。她负责市场、品牌、报批、接洽,每次演出都是独立项目,运营模式是“高度流动的小规模协作体”。6个人能办千人秀,10个人撑起整场剧目。
有一本书叫《流动的现代性》,作者齐格蒙特·鲍曼在里面写道:“稳定已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基本承诺。我们只能在持续的流动中寻找暂时的立足。”现代性从未许诺安稳,它只允诺加速。创业路上的“成功”,不过是一次漂浮的停靠。
她明白,这未必是一套可复制、可长期持续的商业模型,而是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本能。在这个需要不断“自我超越”的社会结构里,自我改写成了最沉默的代价。
她没有喘息,只是在奔跑中努力别摔倒。
04
转向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2024年的开端冷得异常安静。
文旅市场的热度,像掌声一样消散在不动声色的空气中。从春天开始,西安、成都、丽江、大理这些早已“出圈”的目的地继续热闹非凡,但更多的普通城市陷入了寂静。年轻一代的旅行方式正在改变:特种兵旅行、反向游、县城游成为主流选择,而消费本身,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降级。
电影市场首当其冲。暑期档总票房116.4亿元,同比下滑43.55%,剧场演出的票房也节节下探,人们开始重新衡量“值不值得掏这个钱”。而潘丽云最直观的感受,是前一年的合作方,一个接一个“消失不见”。
包场的景区缩减了预算,演出费用被压缩到往年的一半;原本千人剧场的演出也不敢再接,为了降本,她找到一所能容纳一两百人的小剧场,能演自己的剧,也可以做脱口秀、音乐会、魔术表演,用这些内容“吊住流水”。

“我们只敢轻装上阵,连房租都得谈得特别细。”她重新拿起地图,挨个拜访省内的农场、庄园、营地,提供科学秀和魔法秀的同时,推出“半日营”和“周末营”。这不再是“演出”,而是“服务包”,要比去年更灵活、更便宜,也更琐碎。
市场变得越来越碎片化,也越来越不可预测。
2023年是“给景区做内容”;2024年下半年开始,她尝试“为营地提供教育解决方案”。但她自己也说不清,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计划目标定在150万元,不是保守,而是现实。
“我们感觉像是半年换一次活法。”她笑着说,却显得有些疲惫。她常常通过朋友圈观察行业近况。有一天下午,她刷到几个老朋友接连发布消息:曾经供职的教培机构又有几家“爆雷”,一夜清空教师团队,家长群炸锅,公众号关停。
她没有幸灾乐祸,只有轻轻一声叹息:“那些重资产、高成本、极速扩张的企业,太难转身了。”这句话,像是从一位亲历者口中抽出的经验结语,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命运写照。在被不断重塑的行业逻辑里,只有“轻、小、柔”还能勉强存活。
在流动的现代性下,人生就像临时工合同,每一个选择都是暂时的,连身份本身也必须不断更新。潘丽云不再执着于教育二字、不再坚持做内容、不再谈论愿景,转而变成一个随时切换角色的项目经理、演出经纪人、活动策划师、课程设计者、场地协调人,有时是一人,有时是一组人。
这一切变得极度透明。所有合作都变成赤裸裸的“成本与回报”计算,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衡量是否“值得继续”。正如韩炳哲在《透明社会》中写道:“我们失去了沉默的权利,也失去了模糊的权利,一切都要立刻回应,一切都必须自证其价值。”
成功成为一种临时状态,而非稳定结果。你必须不断创造“好点子”,才能不被时代遗弃。
05
“2025年,又是一个新的拐点。”潘丽云这样说的时候,没有悲观,也不再高昂,而是带着一种职业的清醒。她已经不再相信所谓“赛道红利”或“模式复制”,她更倾向于理解一切作为一种“变化管理”的练习。不是如何赢,而是如何不过早出局。
儿童剧的商演红利已然退潮,潘丽云开始转向内容服务,为营地、教培机构、独立教师提供低成本、可交付、可变现的课程产品。这不是一次“进攻”,更像是撤退中的重组。
“我们重新做科学盒子了。”她语调平静,仿佛谈及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但这次不同于2019年那次充满理想主义的出发,而是一次策略性转向。她找来上一位合伙人,为户外探索营开发了5个系列、共30个主题的课程包。课程中设有对比实验、物理原理、小组互动,再以剧本杀形式包装成便携式的桌游材料包。
每一个盒子,既是教学工具,也是教育产品。“就比如‘面包膨胀谜案’,让孩子从‘面包小姐为什么突然变胖’这个线索入手,推理发酵背后的科学原理。”她说这些时眼里有光,像是在讲一出低调又聪明的“微型教育剧场”。
2025年春天,盒子一推出就收获了十余个订单,每单1万元。客户来自台州、赣州、天津,他们用这些盒子丰富课程、润物无声地提升家长满意度。她知道,这条路径不会爆红,也很难被资本追捧,但它能让她的团队稳定落地、不再被风吹来吹去。
这是一种新的“务实主义信仰”:不去讨论教育理念,不再追问价值理想,只问“能不能活下来”,以及“这能不能帮别人活下来”。
在这个语境下,她的改变显得尤其真实。“复盘第一次创业时,我的念头是:一定要把STEAM理念做通。”她顿了顿,“没什么执念了,现在只想活下来。”她说,“哪里有机会,就转头去试;感到危险,就立刻掉头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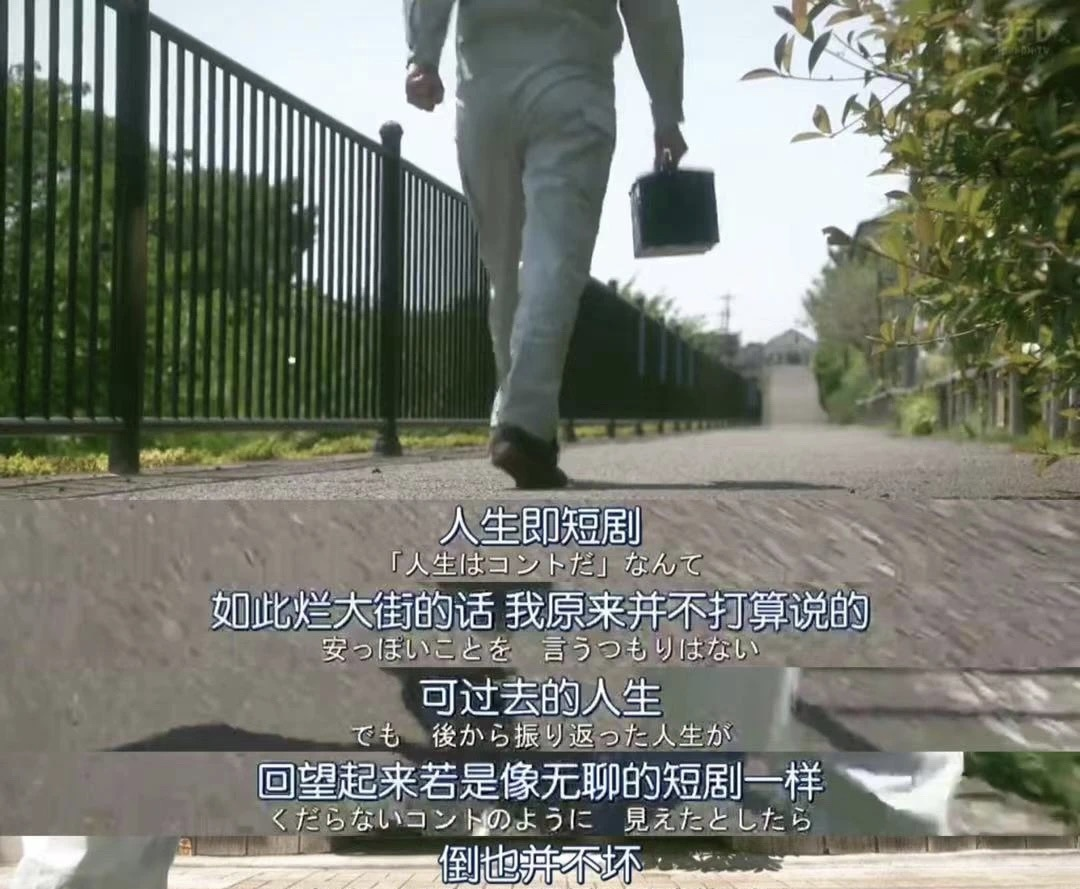
福柯在分析现代社会中的“主体建构”时指出,个体并非天然存在,而是制度、权力与文化规训下生成的临时集合体。潘丽云已不是那个曾在上海校区里喊口号的“教育布道者”,也不是在商场铺展科学盒子的创业合伙人,而是一个由市场环境塑造出的“自我修正型个体”。她以流动应对流动,以模糊对抗模糊。
她的经历,也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大的隐喻:在这个没有剧本的时代,创业者成为了最原型的“西西弗”,不断推着新的石头向上爬,明知终会下坠,仍不放弃调整姿势与节奏。
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中写道:“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。”不是因为他成功了,而是因为他知道,即便没有终点,他也依然可以选择怎么走下去。
潘丽云没有大获全胜,她只是还在场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得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