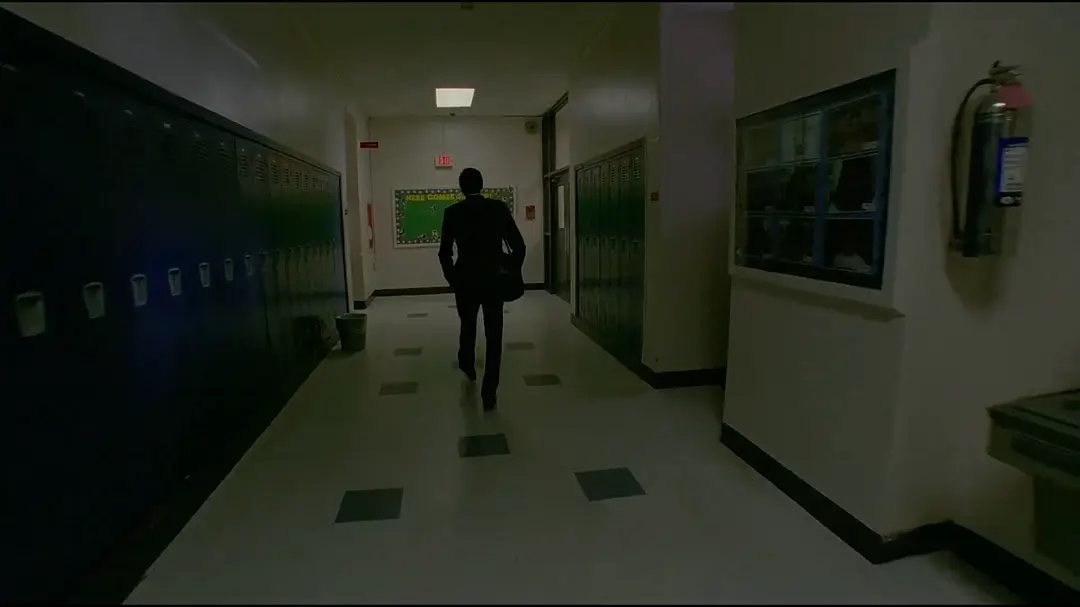
图源:《超脱》
“二茶”是芥末堆的一则小栏目,它可以有多重意思。一则指二窨茶,茶叶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下发酵和蒸热;再来寓意二人品饮对谈,漫天卷地的聊聊二手故事,如人饮茶,甘苦自知。
曾经,它是孩子们离开乡土、抵达未来的必经之路;如今,却像一座缓慢下沉的站台。榜单不再闪光,课堂里流失的不只是学生和老师,还有最后的信任。县中的退场,不只是教育的败退,而是整整一代人被困在原地。
李晓,既是县中走出的孩子,也是后来在世界各地实践教育的人。他在沙特的舞蹈课堂里,看见小女孩们脱掉鞋子在木地板上旋转,在印尼的咖啡馆里听青年辩论哲学。再回望东北的县中,只剩下沉默的榜单和潜规则的暗道。两重身份之间的落差无需多言:教育曾经是一些人的出口,如今却成了困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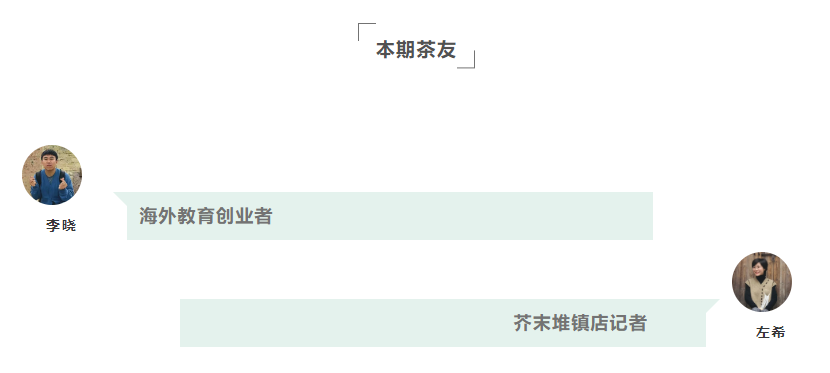
出口与困局
李晓:县中的危机,不只是学校在衰败,而是整个县域社会在悄然退出教育竞争。它不再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入口,而像是一条逐渐封闭的路。
左希:这个判断从哪来?是个人经历带来的,还是一种更普遍的趋势?
李晓:更多源自我的经历。我出生在东北一个资源枯竭的城市,父亲是高中数学老师。我靠数理化走出县城,后来在北科、清华读书,又进入教育行业做海外业务。但每次谈起县中,目光还是会回到父亲曾经教过的那所学校。
左希:在你记忆里,县中是什么?荣耀,还是束缚?
李晓:在更早的年级,学校里还带着点荣光;可到高中我去了大连,差距才真正显现。老家的那所县中,学生早六点到晚九点、月休半天,成绩却一路下滑。1999年以后再没有清北,今年几乎连211都没有。
左希:不只是分数的问题吧?
李晓:是。最明显的是师资的断层,年轻人来了又走,骨干教师调走不回。清北已经断档十多年,榜单年年空白。学生在流失,老师在流失,县中渐渐成了一具空壳。
左希:所以你说的,不只是学校在败退,而是整个县域社会在抽身。
秩序的反差
左希:你小时候是在县里读书的吗?
李晓:是的。小学、初中都在老家读。父亲经常在家里备课、批改作业。我从小数理化成绩就不错。只是后来出国做教育项目时,我才真正意识到另一种路径。
左希:什么样的场景?
李晓:在沙特的一节舞蹈课上,我看到小女孩们脱掉鞋子,在木地板上旋转;在印尼的咖啡馆里,青年们自由辩论社会学、博物学、哲学。那一刻我才明白:教育不是分数训练,而是一种让人有勇气去开口、去表达、去呼吸的秩序。

沙特女孩在校园中训练舞蹈
左希:和你当年的县中比,最大的落差是什么?
李晓:县中更像一台巨大的机器。学生从早六点到晚九点,一个月只放半天假,像零件一样被安排好节奏。所有的努力都朝向分数,却没人关心你是否能开口、是否会思考。拼命程度更甚,结果却更差。
左希:可是你还是考出了好成绩。
李晓:2005年高考,我排进了全县前十,那是我离开县城的通道。可同学们呢?很多人没那么幸运。有人勉强考上普通二本,毕业后进了电子厂,拧螺丝十二个小时,月薪五千,至今困在流水线上。
左希:类似的场景最近在一段视频里也出现过。一家劳务中介面对排队的青年人大声嘱咐:“面试时都说自己是高中或初中,不要说本科,本科、专科一定会被刷掉。” 一句喊话,足以击碎信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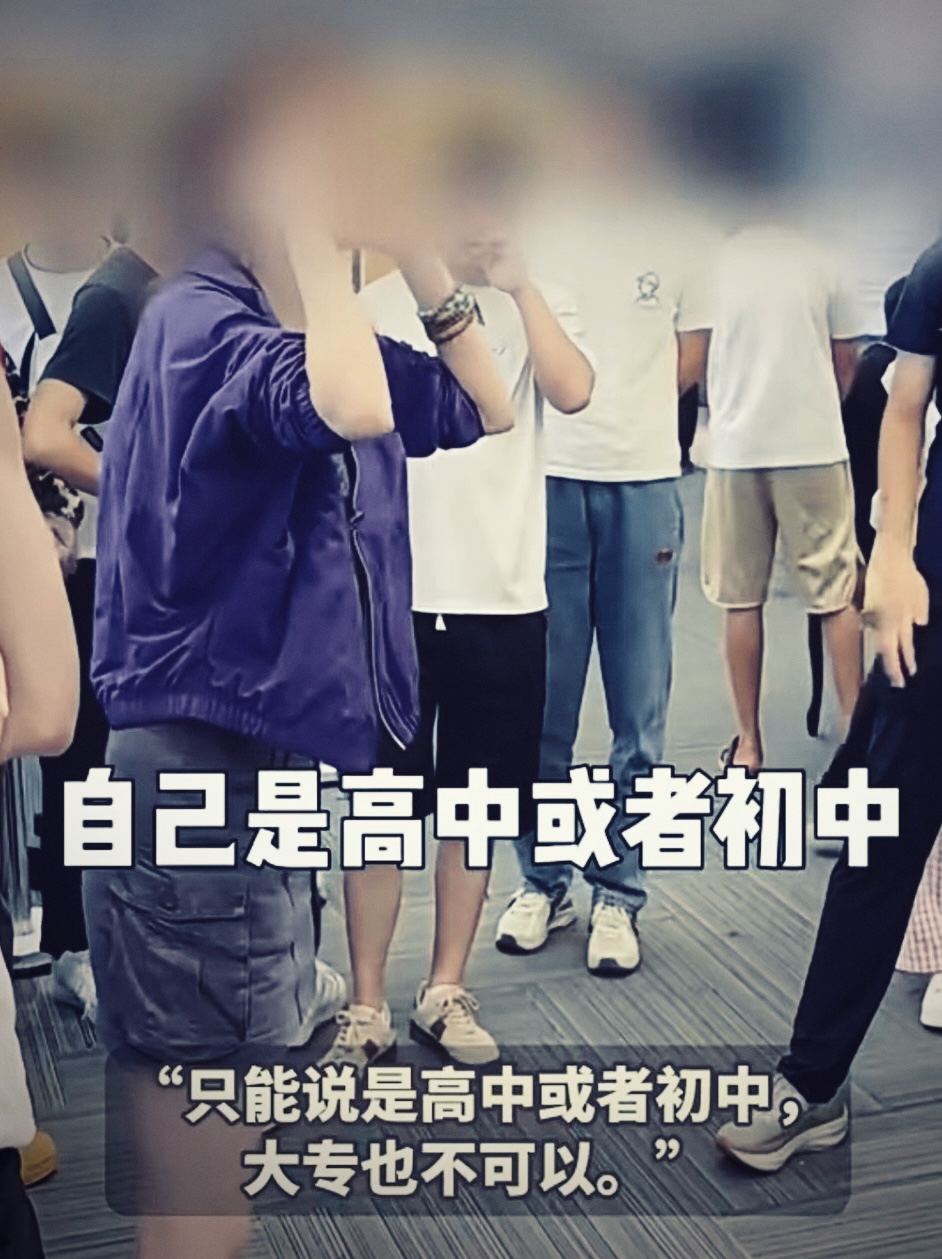
图源:网络视频截图
左希:二十年前和现在的县中,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李晓:二十年前,普通孩子还有可能凭分数突围。二十年后,县中已很难再成为通道。那些被筛选留下来的学生和老师,往往都没有选择,只能硬撑。榜单的沉默,只让我感到一种彻底的无力。县中不再是阶层跃升的梯口,而只是囚困。
县中的坠落
左希:县中的问题,最核心的是什么?
李晓:不是某一个点,而是整栋大厦同时松动。
左希:生源的流失最直观?
李晓:升学记忆已经断档。条件好的家长早早把孩子送到市里,留在县中的,只能在有限的农村学生里“优中择优”。向上的路越走越窄。
左希:师资呢?
李晓:老一代陆续退休,新来的多是普通师范毕业,甚至靠关系进来的。更糟的是,教职被交易化。有人花钱买个班主任岗位,一年靠收红包就能回本,还得层层打点。这条灰色链条挤压了真正想教书的人。
左希:资源和制度层面?
李晓:我老家所在的城市,是全国最早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。人口流失、财政紧张,有限的资金都被集中到市重点、省重点,县中只能一年比一年缩。2015年以后,县中规模不断缩减,招生班数一年比一年少,新老师几乎进不来。职业教育被剥走,分流功能消失。再加上政策层层下压,所有人都被同一套表格和考核锁死,几乎没有回旋余地。
左希:最后是观念?
李晓:是的。家长觉得不送礼就“不公平”,学生怀疑努力没意义。教育的信任和激励机制在消散,性价比不断被质疑。县中成了一张越收越紧的网,把人往下拖。它还在,却越来越像一个被掏空的符号。当教育失去托举的力量,县域社会也将失去连接未来的最后一根线。

断裂的阶梯
左希:你提到县中正在失去出口。那些考出去的学生,后来过得怎么样?
李晓:很多人一直徘徊在边缘。我认识个年轻人,从西北一个县中考上普通二本,毕业正赶上疫情,几乎没有机会。去年他骑车去深圳,在电子厂做流水线,日十二小时,月薪五千出头。他说想攒钱申请工签出国,一年过去,还在车间里。
左希:所以,考出去,并不等于走出了命运的困局。那留在县城的孩子呢?
李晓:也没更好的路。现在县中的学生多来自农村,家长几乎无路可选。厌学、叛逆、网瘾屡见不鲜,学校和家庭都拿不出解法。稍微宽裕的,会把孩子送进军事化管理、戒网瘾或所谓矫正机构,收费不低,多半是二次伤害。
左希:你身边有没有特别刺痛的案例?
李晓:有。一个侄女因为没给班主任送红包被区别对待;一个朋友的孩子因校园排斥陷入严重的心理困境;还有更极端的,因性别认同被家人强行送进戒网瘾学校“矫正”,在那里遭受身心双重压迫。
左希:这听上去,已经不是教育的问题了。
李晓:是的。前段时间,媒体曝光出四川江油一名初中女孩遭长期霸凌、围殴的视频,刺痛很多人。它不是孤例,而是常见的潜疾:孩子缺少安全感,学校护不住,家庭也常常无力。
左希:这意味着什么?
李晓:意味着“出口”不再成立。走出去的人,多半停在城市边缘;留下的人,被困在校园阴影。教育已不是阶层跃升的通道,而像一个被动的消耗系统。人才走了,经济补不上,信任随之松动。二十年前,普通孩子还可能凭分数突围。如今,阶梯一节节塌下去:县域空心,流动停滞,代际的希望被一点点磨掉。当教育失效,社会风险开始在校园和家庭中提前爆发。
两种逻辑的交锋
左希:你在海外工作时,见到过哪些不同的教育场景?
李晓:印度,我感受到的最深,是教育的分层和多样。最顶端是少数人能进入的精英院校,比如印度理工学院、管理学院,它们几乎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进入全国的中上层社会。再往下,是层次分明的私立学校:好的私立学校强调英语教育,面向城市中产;更多则收费低廉,与公立学校差别不大。与此同时,农村公立学校往往缺老师、辍学率高,但社会里还有宗教学校、NGO办的社区教育项目,以及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技能培训班。
左希:听起来比县中复杂。
李晓:对。这样的分层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。精英院校是金字塔尖,但底部学生也可能通过技能培训、社区项目找到一份工作,哪怕只是电工、司机,也算有过渡的通道。和县中的“二元逻辑”不同,要么考学成功,要么坠入底层,印度的教育更像是一张布满裂缝的网。网眼很大,掉下去的也不少,但至少还有横向的缓冲。
左希:除了印度,你还见过类似的情境吗?
李晓:在墨西哥偏远村落,我遇到过由社区主导的小型教育项目。当地年轻人被招募做导师,用母语编写教材,把文化传统融进课程。学校破旧、资源匮乏,但孩子们仍能在熟悉的环境里学习,保有身份认同。这些社区教育更像一块支撑的土地,虽然狭小,却能让孩子在熟悉的文化里落脚,不至于彻底坠空。

锡那罗亚州一所公立小学以社区学习中心模式运营
左希:放在一起对比,差异更加明显。
李晓:对。一边是多层次的选择,即使分层、拥挤,至少能试探不同的道路;另一边是单一的出口,考不上就没有退路。县中孩子的命运,像被推到一道狭窄的崖口。我常觉得,中国县中的崩溃,与西方社会的教育精英化或特权化有某种相似:资源集中,底部失稳,普通学校逐渐失去吸引力。
左希:表象确实类似,但机制也许不同。西方的教育精英化,更多是市场和学区制度造成的静态分层,门槛是房价和学费。而中国县中的陷落,则是行政集中、人口外流和升学资源虹吸导致的整体被掏空。前者是固化机会,后者是抽空生态。速度更快,也更剧烈。
左希:你既是县中走出来的孩子,又是全球教育的实践者,这两种身份会让你怎么看待这些差异?
李晓:这正是最复杂的地方。在印度的昏暗补习班、墨西哥的村落课堂,我看见教育仍然是向上挪动的台阶;回到东北老家,迎面而来的却是冰冷的分数线和无形的规则。那一刻你会发现,教育既可能是跳板,也可能是囚笼。
对未来的想象
左希:你一直在强调“出口”。那县中失去出口之后,意味着什么?
李晓:县中曾经是普通孩子通向现代性的门槛,是县域社会与城市保持连接的桥。它的衰落,不只是学校的失败,而是整个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想象。
左希:可是,县中曾经托举过那么多人完成上升。你是不是低估了它的韧性?
李晓:韧性当然存在过。但当生源流失、师资断层、财政收缩这些力量叠加时,它已不再是一座桥,而更像是一处被遗弃的渡口。人口、教育、经济三重脱钩,让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,也失去了未来的方向。
左希:听上去,这已经超出了教育危机,触及到现代性的根基?
李晓:对。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象征制度,它维系着人们对“努力值得”的共同信任。县中的崩塌,就是这种信任的崩塌:孩子不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,教师不再相信教学有尊严,家长也不再相信教育能带来流动。当这种信念系统松动,社会就会陷入某种深层失序。
左希:你在海外看过类似的场景吗?
李晓:在印尼一些小镇,哪怕条件拮据,咖啡馆角落里仍会摆上一张书桌,提醒人们教育还在。可在县中,孩子仍在向上攀爬,但社会已经把梯子抽走。最致命的匮乏,不是物质,而是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。

印尼乡村教育实验项目,学校嵌入村落环境中
左希:容纳了中国超50%学生的县中,失去的不只是教育本身。
李晓:是的。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对“无用之物”的尊重,最终也会失去对人的尊重。今天的县中正是这种逻辑的缩影:孩子被压缩成分数和排名,教育也失去了作为承载未来想象的场所的意义。
左希:当效率与竞争成为全球教育的关键词,人们的休息权、失败权与不参与的自由都在消失。所以,真正的危机,不在于多少孩子能考上大学?
李晓:没错。真正的问题在于,我们是否还相信未来值得抵达。一个健全的社会,不该只有一条单一的轨道,而要容纳不同的节奏:有人全力奔跑,有人选择慢行;有人追逐上升,有人安于寻常。哪怕背离主流,也应当被善待。教育既是个人的出口,也是社会的容器。
左希:可现实是,县中的孩子既追不上城市的步伐,也得不到放慢脚步的体面。他们被困在两头落空的夹层里,不知往哪去。县中并非单纯的教育危机,而更像是现代化的裂缝被放大的一面屏幕。它让我们提前看见:通过教育实现上升的信念,正在瓦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