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本文图片由AI生成
今天的留学市场,早已不是“普遍热”或“全面冷”这类标签可以概括的。它真正折射的,是一个社会在面对未来路径时的内部分化:
有的家庭,多年前就为孩子铺设了通往海外的桥梁,顺流而下;而另一些,则在多重考量后主动回调,转向更可控、成本更低的教育轨道。
这些差异,并不总是能力或理性的体现,更多反映出人们对现实风险与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同理解。
一、失速起跑线:当“出国”不再是光荣的背影
2025年6月,英国内政部公布数据显示,在截至当年6月的统计周期内,英国共发了431,725 份学习类签证,其中中国内地学生签证数达到 99,919,位居所有国家首位,占比24%。与此同时,加拿大移民、难民和公民事务部发布的官方报告显示,截至2024年9月,加拿大境内有效学习许可持有者为 1,297,365 人,其中来自中国的学生达124,445人,占比9.7%。数字依旧强劲,仿佛一切未变。
但几乎在同一时间,多个一线留学中介的顾问反映:朋友圈里晒offer的家长越来越少,签约转化周期也比往年更长。哪怕是“美本藤校大满贯”的案例,也难再引发全民艳羡式的刷屏效应。
“每年三月到六月是offer发放高峰,以前一天能转十几条录取截图。现在,几乎没客户愿意公开。哪怕拿到康奈尔、芝大,家长也只是低调转发,甚至干脆不发。”一位从业十余年的顾问告诉我们。
曾经象征阶层跃升与教育成功的出国,正经历一场意义上的沉降。
康晴的决定是其中一个注脚。她曾在体制内工作,在孩子中考失利后,毅然卖掉北京的一套房,将女儿送去英国读A-Level,把留学视为家庭的最后一条捷径。但做出这个选择后,她主动退出了几个“留学家长群”。她说:“太贵了,说出来也不光荣,别人会以为我们是疯了。”
与此同时,另一些家长则选择慢下来:放弃国际班、改走高考路线。留学从“必选项”变成了“再考虑一下”的备胎。这种转向背后,实则反映了客户结构的再分化。
“一线城市的家庭犹豫了,反倒是地级市客户签得最果断。”一位原头部机构的销售负责人告诉我们。在他看来,合肥、盐城、烟台这些城市的家长不再执着比价或排名,而是更关注通道能否稳妥落地:“能不能包录?能不能分期?”他用“跑得快、看得准”来形容这批新客户的决策路径。
在这种节奏差异中,老牌中介机构也开始出现裂痕。自2023年底以来,部分一线城市的留学机构陆续传出关店、裁员消息。多位业内人士反映,2024年春季以来,顾问业绩普遍出现明显下滑,一些平台同比下降三成以上。不少人转向“跳水价”自营,以“卷服务”的方式维持收入。一位广州某国际部的顾问说,“这两年最明显的感受是:客户不再执着于出国,而是更愿意听国内方案,甚至有人直接问我有没有国外线上硕士。”
而在中介之外,一种新的咨询师形态正在浮现。以叶子为代表的“全案咨询师”,不依附平台、不走流水线,靠朋友圈与熟人推荐完成转化,强调“走得早、走得稳、别中断”。她的客户中既有从小学就开始规划的家庭,也有临时调整方向的突发切换者。比如,一户杭州家庭原计划通过学区房走高考路线,因政策调整未能入读目标学校,最终转向澳洲升学,将全部资源投入另一套路径。
与此同时,舆论场中的留学语境也在变化。早期小红书上流行“申请牛剑攻略”“英美学姐经验贴”,如今热度转向“避坑指南”“低价留学”“能留下来的专业”等现实取向。一位内容运营者直言:“大家最关心的不是学校牌子,而是能不能留下、回报率高不高。”
这种变化,不完全是冷静的表现,更像是一种迟疑。原本通往“外部”的路径,正在中途分岔。

而在教育叙事的上游,这种路径分化愈加明显。原本主导升学节奏的,是一套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启动的“早规划”路径。当下,越来越多家长开始质疑这套路径的必要性:“如果以后出国这条路走不通,我们是不是该早一点调整?”
一部分人仍沿着惯性轨道滚动向外,另一部分人开始重新计算这趟旅程的得失,更多人则在系统之外,选择原地等待。留学,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分化的象征性路线。
二、分岔的轨道:一个社会,两种路径
“不是非要出国,但这条路我们不能不准备。”这是许多家长在咨询时给出的答案。
在他们眼里,留学更像是一条启动之后就无法停止的流水线工序。某中型机构顾问徐遥曾在北京一场说明会上感受到这种“执行感”:“家长不是来问要不要出国,而是来问今年还能不能走。”中介的任务,也从寻找合适学校,变成了“逐一卡住每个节点,别出错”。
这一逻辑正在重构留学的语法:不再强调孩子的兴趣和能力,而是强调履历完整性。一位国际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提到:“有学生英语一般,但家长坚持送去英国,说那里的压力大,孩子才不会松懈。”这已不是学生的选择,而是家长在做风险配置。
顺着这种心态,留学机构纷纷推出颗粒化套餐:英美双申、低龄夏校、DIY+文书精修……本质上都是预制方案。“就像买保险一样,买了不一定用得上,但没买就觉得不安心。”一位顾问说。
一旦上轨,停下来反而更难。“从小学就读国际课程了,怎么高三突然说不去了?”“签证下来、文书写完,临门一脚撤了,家人也难接受。”一位南京家长形容:“我们就像坐上了快车,只能往前,不能跳车。”一名国际高中毕业生说得更直白:“不申请国外,我都不知道还能申请什么了。”
2025年夏,北京一所知名民办国际高中的升学指导老师注意到一个细节:往年家长会上,最常被追问的是美本排名;而今年,越来越多家长选择会后单独询问,“如果成绩不理想,还有别的路吗?”同一时间,在西南某省一所县级中学,原本计划开设的国际班因报名不足十人被取消,学校给出的理由是“资源浪费”。
两个场景,像两条平行轨道,同时存在于一个教育系统中。留学,从未像今天这样,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分化面貌。
“同样的规划费用、申请流程、时间成本,2025年的家长反应完全不同。”一位华东地区大型留学机构的区域负责人告诉我们。在北上广深,一些家庭开始收缩路径,转而考虑国内选项;而在二三线城市,则有新的中产群体加速外推。他举例:“有位来自中部地级市的家长,在咨询时连GPA都不懂,但坚定要送孩子去澳洲。他不是因为了解教育理念,而是觉得‘窗口还开着,再晚就来不及了’。”

2025届国际学校的毕业生选择,也印证了这种结构性分化:选择港澳高校的比例达到35%,选择中外合办的比例为28%,两者相加首次超过直接出国的25%。
这种“错峰式前进”,背后是资源和心理的分化。高净值家庭依旧将留学视为身份重组的必选项,技术移民家庭则把它当作迁徙路径的副产品。而传统中产,却越来越进退两难:既承担不起早规划的高投入,又没有勇气All in。
“不是出国的人变少了,而是出国的人变了。”一位留学顾问这样总结。这并非理性决策的差异,而是社会结构裂缝的浮现。在这套机制中,暂停几乎不再被允许。项飙所说的“Gap的消失”,在这里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。留学,不再是一场主动跃迁,而是一条无法中止的单向轨道。
三、理性失效:留学成资产负债表缩水的“保险单”
留学,正在失去它原本的语义。它不再是一场关于全球视野与教育理念的选择,而更像是一场家庭层面的风险对冲,是为了避免孩子落入不可控局势而预先缴纳的一笔“保险费”。
2025年8月8日,《泰晤士高等教育》刊发评论指出,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行正在动摇中产家庭送子出国的能力。文章预判,未来中国留学或将回到世纪初的状态:只有极少数家庭能负担。
这并非杞人忧天。在过去十年里,房产与教育构成了无数中产家庭的双重支撑结构:前者提供确定性,后者保留上升的可能性。而房产,往往既是孩子的学区门票,也是日后出国留学的储备池。
如今,这一逻辑正在松动。
2022年,北京一对夫妻以570万元购入西城区一套30平米学区房。三年后,同户型挂牌价仅为345万,资产缩水四成;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周边的房源,2021年还值739万,2025年夏只剩434万;广州天河区某小区从16万/平跌至7万,腰斩式回撤。二三线城市的调整更为剧烈:根据格隆汇2025年6月数据,温州房价近三年跌幅高达54.3%,郑州46.8%,青岛、石家庄、徐州等多地超过四成。
当房产不再具备换取留学预算的能力,家庭的资产配置逻辑也随之失衡。那些原本“换房”的计划,被迫转换为另一种路径的押注。至少在现阶段,后者看起来更可控。
在杭州一场家长分享会上,一位刚升入初中的母亲直言:“原计划咬咬牙换套房,但看着房价跌成这样,我突然想,不如把这笔钱留给孩子出国。”她的声音,在台下引发了一串点头。
这不是个案。据一位头部留学平台从业者透露,2024年上半年,虽然签约总人数略有下滑,但初中以下年龄段的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15%。一些机构设立“低龄部”,为小学四年级起的学生量身定制路线图。
选择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。近两年,一些机构专门推出匈牙利、马来西亚、土耳其、阿联酋等兜底路线。不求最好,但求能走。

在一线城市,这种“早转轨”多由资产缩水驱动;而在中部、南部城市,则往往来自对升学制度不确定性的防备。这种决策,不再是对教育的“理性投资”,而更像是一种被动应激。
“现在出国的家长,不是理想主义者,而是现实主义者。”一位独立顾问说,不是奔赴未来,而是为了规避意外。一旦未来失控,至少还有一条路,还没有被彻底堵死。
四、撤退与前冲:2025留学行业的错位现实
2025年的留学行业,正在呈现一种错位的双重图景:一方面,更多家庭选择更早启动留学规划;另一方面,更多中小机构则在悄然退场。
5月,新东方发布《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2025》,收录了8000份留学家庭样本。在学生的意向国家中,英国、美国、香港位列前三,爱尔兰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阿联酋等“非主流选项”快速上升,香港更是首次跻身前三,爱尔兰则从冷门变为“黑马”。
ACG、斯芬克、启德等细分平台的2025申请季数据也佐证了这种趋势: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国的艺术、酒店管理、传媒与设计类专业offer数显著增长。从“冲藤”到“保录”,从美英顶校,到布局港新澳,路径变迁背后,是风险预期的重新调配。
在服务端,留学机构的分化也已肉眼可见。
一线城市的大型平台正强化数据能力与高端定制,比如启德建立“录取数据库”,展示录取时间线与评估因子,而大量中小机构则在加速轻量化、颗粒化。上海某教育机构走访了几十家存续同行后发现:服务流程被拆解为“选校—文书—签证”三项,家长可像点菜一样分项付费;团队结构普遍压缩到5人以内,顾问多为“无底薪+签约提成”的兼职模式。“人力成本砍掉60%,反而活得更久。”这是不少幸存机构的共识。
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轻装上阵的余地。2024年1月至7月,全国注销留学机构达212家,平均每天消失一家。三线及以下城市中,曾依赖地推与门店网点的“地市分公司”体系正在系统性退场。某省头部机构一年内关闭了14家地市分部,仅保留省会直营门店。
在成都、合肥等二线城市,另一种微型生态正悄然形成:由个体顾问组成的“顾问工作室”正在联盟化,形成聚焦港新理工等细分赛道的松散网络。例如成都桐梓林一带,已集聚20家顾问工作室,彼此独立却又资源共享,成为一种“中产教育焦虑平台化”之外的另一种缝合机制。
整个行业进入了“高龄早熟 + 机构碎片化”的结构状态:家长启动更早、押注更窄;机构服务颗粒化、团队轻量化;中介生态从连锁门店向分散个体漂移。留学中介不再是教育路径的陪跑者,而是按焦虑分工的“家庭战术团队”执行者。
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底色,是家长不愿被困住的惶恐。
一位母亲这样解释孩子出国的决定:“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大学,而是不想被留在原地。”她并不否认国外教育的问题,却更惧怕国内升学系统的锁闭和资源的收缩,“我们只是想避开一次结构性落选。”

从一线与中部城市的调研来看,许多曾在国际学校、留学中介或外语培训机构一线工作的从业者都表达出类似的判断:“孩子其实没那么想出去,但家长比任何时候都坚决。”仿佛留学已不再通往理想教育路径,而是对社会走势的提前响应。
这种角色的错位,正在悄然改变留学的象征意义。
它不再指向开放、探寻与自我塑造,而更像一种社会结构对个体的默认要求:你不能停下,不能犹疑,不能走错一步,必须持续奔跑、获取资格、规避风险,以免在某个关口被甩出轨道。
当人生路径不再容许暂停或偏离,只剩下连续的推进与应对,留学也就从“目的地”变成了“策略”,成为个体尚未被彻底困住的象征。一个孩子出国,不是因为志趣高远或人格独立,而是因为他必须规避系统性的不确定:考试、户口、身份、竞争、焦虑。
“远方”因此成了一种伪命题。
如果顺着这个视角再走一步,会发现更深层的转变:教育的意义本应关乎“自我建构”,而今天,它正在被“对外应对”所取代。
在宏观数据的光亮背景下,这个行业正陷入一场悄无声息的重构。
从行业视角回望,留学曾是中产家庭押注未来的“黄金通道”。2000年,首批68家中介机构获得资质,留学市场化正式启动,随后大量中介机构与语言培训平台兴起,IELTS、TOEFL培训产业爆发;2010年代,国际学校、标化考试与留学中介构成了一整套可复制路径,留学被广泛视为通往更高阶教育、更广阔职业可能与身份跃迁的象征。自2020年起,地缘政治紧张、海外通道收紧、身份焦虑叠加和市场高饱和,这条通道变得愈发不确定,曾经的改变命运,更像是一次“延迟落选”。
到了2025年,留学仍在继续,但它承载的意义,已悄然改变。曾主导留学潮的长期主义,正在被风险厌恶逐步取代。在多位从业者的描述中,一个词被反复提及:“保底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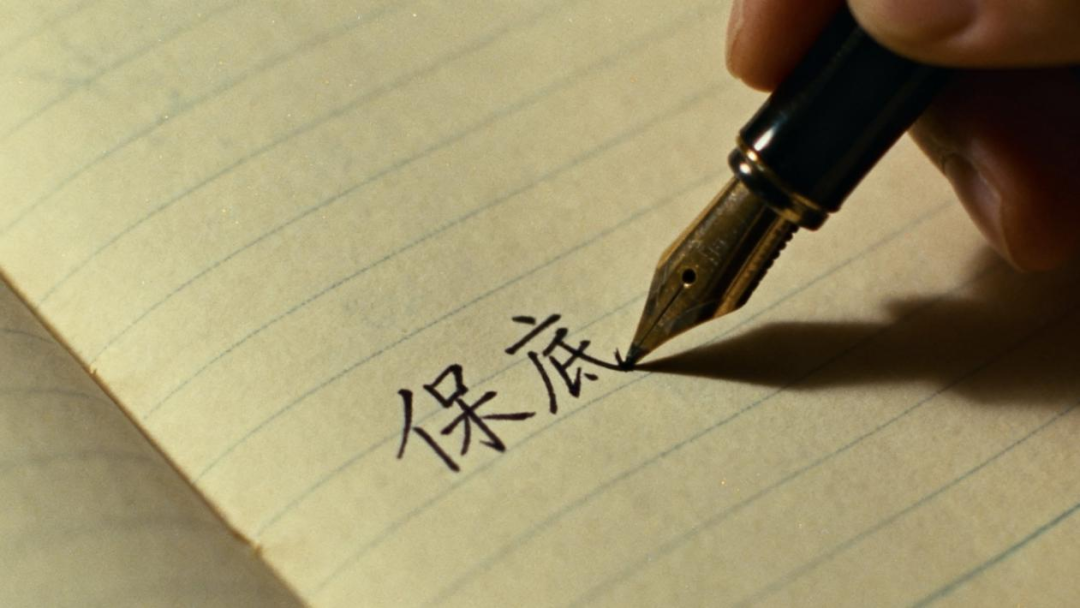
2025年夏天,我们走访的某一线城市高端中介平台中,暑期业务量虽有回暖,但产品方向悄然改变:不再是高排名学校和热门专业,而是那些具备后路属性的一条龙通道:可延续居留、落地陪读、就业转签。在这种路径中,学习本身正被压缩为一环流程,真正影响决策的,是能否延展出一条更稳妥的人生路径。留学的核心逻辑,从教育转向对政策和制度通道的预判。
留学,前所未有地像一场风控模型:不能太贵,不能太偏,不能太赌,也不能太慢。
这也是一种对国内路径系统性焦虑的映射:中考分流的不确定性、精英教育的供需失衡、阶层跃升通道内卷化,每一个节点都在强化非此即彼的竞争逻辑。当所有教育选择都沦为风险管理,未来的想象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。那意味着:决定人生节奏的权力,正在从个体手中滑落,转而交由系统、算法、政策与预期主导。
所以,我们最终真正讨论的,从来不是“留学值不值”,而是“未来”这件事,已经越来越难被想象、被规划,也越来越无法被抵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ET2025教育科技大会
教育有AI,学习无界!
11月17-18日,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
凭VIP门票,领取限量版 《2025教育行业蓝皮书》一本
